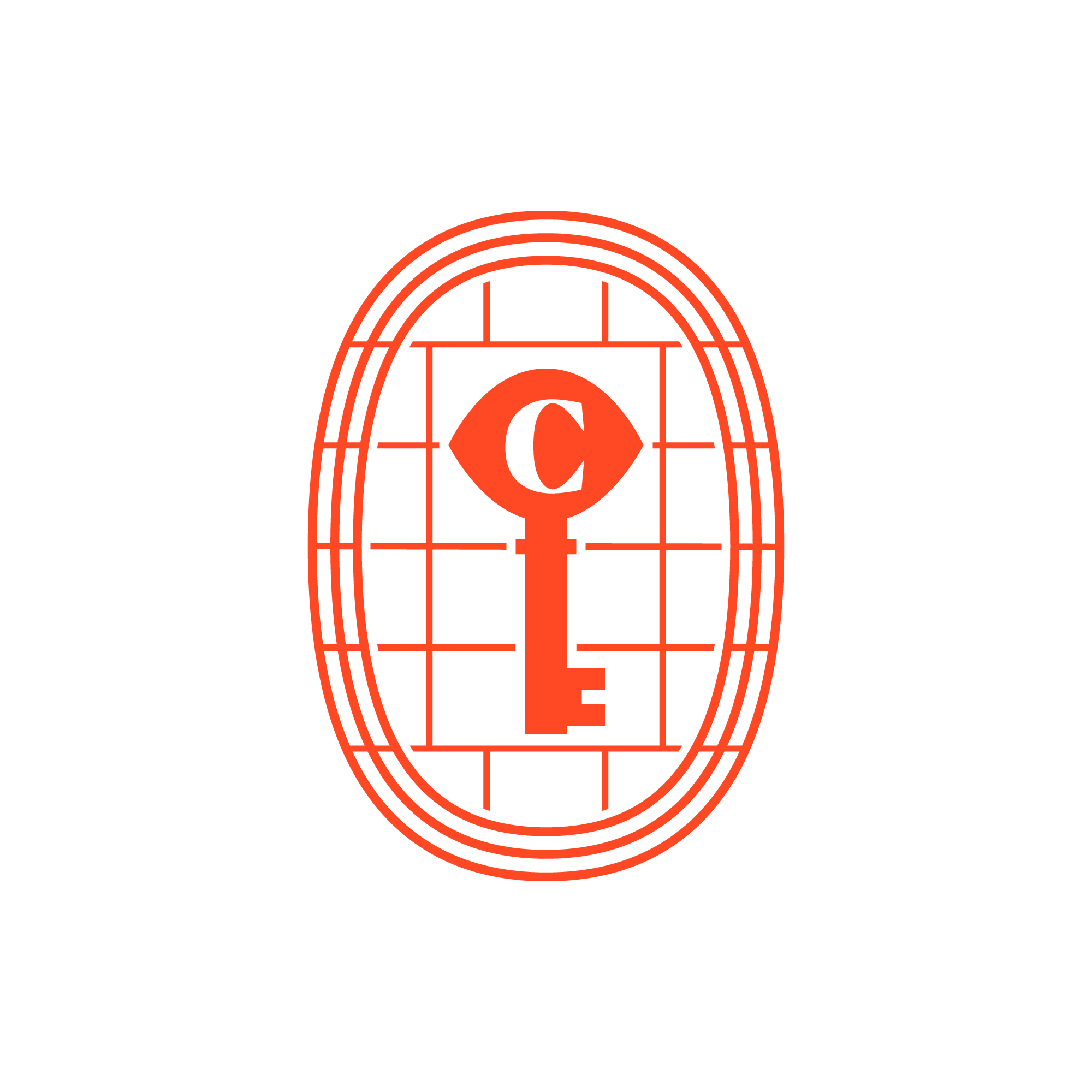白蘭樹下創辦人
農夫默默耕作,不時飄來天然肥料的氣味,放眼望去,四處都是田園和低矮的小屋,這種彷如歸園田居般的生活環境,卻確確實實發生於香港:

「大家都知道,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耕生活是很辛苦的,怎會比得上能夠激發腎上腺素的打獵?為甚麼人類要放棄刺激的狩獵生活,改為過農耕生活?」相對沉默寡言的Joseph一談起酒,便變得眉飛色舞:「那是因為農耕生活可以飲酒。飲酒開心嘛。」
由狩獵採集社會過渡到農業社會,幾乎是所有人類社會的必經階段,一般相信,那是因為人類渴望穩定,對他們而言,可能是渴望酒精。在八鄉這間老舊村屋中,竟藏著一個掛著「花天酒地」牌匾、裝潢典雅的微型酒吧,架上陳列一枝枝獨特的方型酒瓶氈酒,等待調酒師沖配。那就是本土品牌「白蘭樹下」(Perfume Trees)兩位負責人,阿傑和Joseph的「秘密基地」。

「白蘭花只有早上最香。它的香氣很快散走,因此一定要在早上摘花,中午12點前蒸為原液,再寄到荷蘭的工場讓他們精製成氈酒。」他們解釋道。由於牌照問題,要在香港製作蒸餾酒非常難,「我們嘗試過用不同花,就只有白蘭花最適合。從前街上有很多賣白蘭花的婆婆,那是一種代表到香港的味道;在試酒會中,最多人辨認到的香味也是白蘭花。」
阿傑和Joseph以大埔林村的白蘭花,加入陳皮、龍井、檀香和當歸等東方材料釀出氈酒「白蘭樹下」,那是一種與別不同、只屬於香港的「型格」:「做人最重要就是型。當初想做調酒師,都是因為型而已。」阿傑說。「我15歲開始第一次飲酒,因為當時在外國讀書『無王管』,後來開始做調酒師,大概也有18年了。」阿傑笑道:「2012年回來香港,可是香港生活艱難得多。」
阿傑回到香港後,除了擔任調酒顧問、創辦調酒學校外,同時也會定期教授僱員再培訓局旗下調酒課程,過程中便認識了學生兼拍檔Joseph。與自小浸淫在酒精世界中的阿傑不同,Joseph過去只是喜歡喝酒,卻沒有深入研究。Joseph當過十年公立醫院護士,在工餘時間學習調酒,便和導師阿傑一拍即合:「在大機構工作沒有成就感,我想創造一點自己能控制、持久的東西。」Joseph解釋道。
「我覺得人是需要飲酒的。為甚麼下班時間會有Happy hour?就是讓人在下班回家之前,透過酒放下所有壓力。」阿傑說,「不同社會都有自己的酒,可能釀制方法不同、飲酒習慣、時間不同,但酒本身是平常不過的東西,有些人卻會妖魔化酒。外國人小時候就會認識酒,現在香港大眾對酒的認識還很少,我一直很堅持教書,因為教育很重要,社會大眾需要認知、需要品味。我很討厭『酒精害人,影響一生』那種說法,為甚麼酒精就會是害人呢?諷刺的是我任教其中一部份課程就是政府開辦的,政府又同時對人說『酒精害人』。」
「飲酒當然不健康,但吃飯也不健康,吃叉燒飯更加不健康,但就是好吃嘛。人有自由意志,在一個理性社會,只要人有背後的知識、清楚知道後果,就會懂得選擇,可以讓他們決定做還是不做。」Joseph笑道:「政府就好像一個老姑婆,甚麼都討厭,才會主張禁酒。」
「我不同意,我覺得飲酒有益健康。對精神健康嘛。」阿傑說道,而氈酒最初誕生時,的確是藥用的,「酒是文化,也是藥。無限制地喝酒才會有危險,但任何東西失去限制也變得危險。」
當去到酒吧卻想不到喝甚麼才好時,很多人都會選擇Gin and Tonic。假如在外國喝Gin and Tonic時,調酒師用的是來自香港的氈酒,那就是阿傑和Joseph夢寐以求的畫面了。在酒的世界中,過去數年最紅的是威士忌,如今氈酒已漸漸成為新主流,他們選擇走一條較多人欣賞的道路,希望白蘭樹下走向世界,讓更多國家和地方留意香港。
「酒是身份認同,比如說大陸人會很自豪自己有茅台。數年前香港人忽然覺醒本土情懷,我們卻沒有一種屬於香港的酒。」Joseph說。「我們想做一種香港人認同的酒。」

Storyteller: @Perfume Trees Gin 白蘭樹下
Text by Wong Yue Hang
Illustration by Midori.